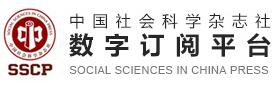最好时光里的阿季:才女贤妻之前,杨绛是杨季康
惊闻杨绛先生去世,悲痛之余亦在感慨,“我们仨”的团聚也许是先生希冀已久。谈起先生,众人多说“最才的女,最贤的妻”,抑或与钱锺书的爱情故事。再不然就是爱女钱媛去世的痛彻心扉……而我们忘了,在成为这一切前,她只是杨季康,承欢父母膝下的阿季。
青春岁月里的阿季,最美年华里的阿季,让我们一起去怀缅。本策划摘自《听杨绛谈往事》吴学昭著,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出版;《杨绛传》罗银胜著,京华出版社出版。

2
|
| 阿季(杨绛)一岁时 |
杨先生清晰记得:“一次,大家摇船到‘青阳地’看樱花。天微雨,抬头是樱花,空中是飞花,地下是落花,很美。同游者费孝通、孙令衔、沈福彭、孙宝刚,还有姚克的弟弟。我总和周芬一起,还有沈淑和周芬同学医预的女生。”
幼承庭训:要有志气树立大志向 劳动获取所得
杨绛,一九一一年七月十七日出生在北京,原名杨季康,后以笔名杨绛行世。
民国初年,其父杨荫杭就任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厅长,由于本省人士必须回避本省的官职,杨荫杭被调任浙江省高等审判厅厅长,住在杭州。他因坚持司法独立,得罪了省长屈映光。屈映光晋见袁世凯时,乘机诬告杨荫杭,说“此人顽固不灵,难与共事”。恰巧袁世凯的机要秘书张一麟是杨荫杭在北洋公学时的同窗好友,帮忙说了好话。这样,杨荫杭才没吃大亏。袁世凯亲笔批了“此是好人”四字,杨荫杭便奉调到北京任职。
杨荫杭夫妇带了杨绛等人到了北京。杨绛是在五岁(一九一六年)时开蒙的。她上的小学是在北京女高师附小,她的三姑母杨荫榆就在女高师工作,杨绛开始有记忆也是在这个时候。
那时候的杨绛欢快活泼,充满童趣,惹人喜爱。女高师的学生时常带着已放学的杨绛到大学部去玩耍,她们陪小杨绛打秋千,蹬得老高,杨绛心里既高兴又害怕,嘴里不敢讲出来。
一九二○年,杨绛随父母迁居上海,她和三姐跟随大姐同在上海启明女校读书,寄宿在校。老家仍在无锡,在上海租赁两上两下一处弄堂房子。在上海期间,杨绛的母亲生下了她最小的妹妹杨必。
杨荫杭认为,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职业可做,一是医生,二是律师。他不能做医生,只好当律师。但是律师职业的风险远比医生厉害,面对黑暗的社会,律师要依法伸张正义,真是谈何容易。杨荫杭嫌上海社会太复杂,决计到苏州定居。
由于租赁的房子只能暂时安身,而执行律师业务则需要有个事务所,所以杨家急需房子,此时有一所名为“安徐堂”的大房子待出售,于是便买下了。
这一建筑还是明朝的房子,都快倒塌了,里面有一间很高大的厅已经破落不堪,当地人称之“一文厅”。
这“一文厅”颇有来历:据说明代大阉魏忠贤当道横行,有人奏称“五城造反”,苏州城是其中之一。有个“徐大老爷”把“五城”改为“五人”,保护了苏州的平民百姓。“一文厅”便是苏州人为感谢这位“徐大老爷”而建造的,一人一文钱,顷刻募足了款子,所以称为“一文厅”。
杨荫杭以一大笔人寿保险费买下了这座没人要的破宅院,修葺了一部分,拆掉许多破的小房子,扩大了后园,添种了花木,修建的费用是靠他做律师的收入。
杨荫杭还教育他的子女要“有志气”,树立大志,杨绛在中学的时候,还听她父亲讲到同乡一位姓陆的朋友有两个在交通大学读书的儿子,“那两个孩子倒是有志气的,逃出去做了共产党。”(据杨绛后来回忆,这两人就是陆定一兄弟。) 杨荫杭还主张自食其力,不能不劳而获,这些都给孩子的心灵塑造产生很大的影响。
杨绛家搬入“安徐堂”后,修葺了一套较好的房子,前前后后的破房子还没拆尽,阴湿的院子里,只要掀起一块砖,砖下密密麻麻的到处都是鼻涕虫(软体动物,像没壳的蜗牛而较肥大)和蜘蛛。杨荫杭要孩子干活儿,悬下赏格,鼻涕虫一个铜板一个,小蜘蛛一个铜板三个,大蜘蛛三个铜板一个。
在杨绛看来,这种“劳动教育”其实是美国式的鼓励孩子赚钱,而不是教育“劳动光荣”。杨绛上学周末回家,发现她的弟弟妹妹连因病休学在家的三姐都在“赚钱”,小弟弟捉得最多。
唐须荌对她的丈夫说:“不好了,你把‘老小’教育得惟利是图了。”
可是这种“物质刺激”很有效,不多久,弟弟妹妹把鼻涕虫和蜘蛛都捉尽。唐须荌对这帮“惟利是图”的孩子也有办法,钱都存在她手里,十几元也罢,几十元也罢,过些时候,“存户”忘了讨账,“银行”也忘了付款,糊涂账渐渐化为乌有,就像他们历年的压岁钱一样。因为孩子们不必有私产,需钱的时候可以问自己的母亲要钱。
肆意的东吴时光:梳娃娃头曾被当做球队吉祥物
阿季(编者注:杨绛)用五年时间修完了六年的中学课程,1928年6月从苏州振华女校提前毕业。按说,这是件令人高兴的事,值得庆贺,可阿季每忆及此往往自叹运气不好,不如不提早一年毕业。因为心心念念进清华大学外国语文学系的阿季,毕业那年,清华开始招收女生,但没有到上海来招生。下一年,阿季原来同班的蒋恩钿、张镜蓉等同学全都如愿进了清华外文系,而以阿季的学业成绩考入清华应不成问题。
阿季要上大学了,这在她家是件大事。
她已考取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和苏州东吴大学。金陵女大录取成绩第一名。东吴的入学考试成绩,初试是第一名;复试第二名,第一名为孙令衔。但学校说,复试第一名仍应是杨季康;因为复试的考题,全部是孙令衔在东吴附中毕业考试时已经考过的。
阿季是家里第一个上大学的孩子,所以除了爸爸妈妈,曾经留洋的姑妈荫榆、堂姐保康、表姐袁世庄以及中学的师长王季玉先生、俞庆棠先生等,也都来关心,提出意见。上女校,较闭塞;男女同学好,男孩子思想较活跃。大家主张阿季该进东吴,多结交一些朋友,可以互相启发,共同切磋,切不可只交一个朋友。
阿季天生的脸色姣好,皮肤白是白、红是红,双颊白里透红,嘴唇像点了唇膏似的鲜亮。苏州太太见了都说:“喔唷,花色好得来。阿有人家哉?”妈妈说:“小呢,上学呢。”她们就说某少爷懂几国“英文”,要为阿季做媒。
阿季进东吴时梳个娃娃头,自忖像个无锡大阿福,不意却被称作“洋囡囡”(也因为她姓杨),当时以此闻名全校。简笔勾画的阿季卡通头像,画在体育馆各类球赛的记分牌上。球员全体照上有一个洋娃娃,是球队的吉祥物。
“洋囡囡是玩具,我怎么成了玩具呢?”阿季起初认为被称做“洋囡囡”是奇耻大辱,很不自在,以后发现同学们并无恶意,也就不介意了。 1930年的东吴校刊上有张图片:底下一堆洋囡囡,顶上一个阿季的娃娃头像,标题是:We are洋囡囡’s。无锡的亲戚都知道了,阿季觉得很没面子。
但阿季很快就克服了她的害羞,大大方方地与同学们相处。和同班同学都“叫应”,除了朱雯,因为他说阿季“太迷人了”,所以阿季见了他不睬不理,整整四年不睬不理。解放前夕,朱雯偕夫人罗洪同到上海钱宅拜访钱锺书,杨先生特喜欢罗洪。从此他们夫妇和朱雯、罗洪,成了多年的老朋友。
我问杨先生:“您在东吴是不是收到许多情书?小报上说当时追求您的男同学有孔门弟子‘七十二人’之多。”
杨先生答:“没有的事。从没有人给我写过情书,因为我很一本正经。我也常收到男同学的信,信上只嘱我‘你还小,当读书,不要交朋友’以示关心。”
杨先生说:“有些女同学晚上到阅览室去会男朋友,挤在一处喁喁谈情。我晚上常一人独坐一隅,没人来打扰。只有一次,一个同学朋友假装喝醉了,塞给我一封信。我说,‘你喝酒了,醉了?——信还给你,省得你明天后悔。’这是我上东吴的第三年,很老练了。这人第二天见了我,向我赔礼,谢谢我。以后我们照常来往如朋友。我整个在东吴上学期间,没有收到过一封情书。”
谈月琴、唱昆曲:阿季原是多才多艺
上海中西女校来的四位女同学:阿薛、阿黄、阿狄和阿俞,也与大家相处很好。尤其薛正,年稍长,会处事,护着小学妹,受到大家敬重。一次朱雯写了一篇《杨朱合传》,将在校内一张不入流的小报上刊登。女同学看到预告的题目,都代阿季不平,薛正招朱雯谈话,朱雯立即将该期小报统统买下销毁。阿季对所有的女同学,尤其阿薛心存感激,至今不忘。阿薛后来从燕京大学毕业,回上海当了中西女校校长。
阿季和周芬都喜欢音乐。周芬会吹笙。阿季和沈淑能吹箫,买了一对同样粗细的九节紫竹箫,三人在校内课余活动时合奏民乐,如《梅花落》之类。阿季还能弹月琴,都是自学的。她们曾参与东吴民乐队的演出。
阿季不只会演奏乐器,还能唱昆曲,那是在家偶然学的。父亲业余研究说文音韵之学,请了一位拍曲先生,向他请教某些文字的发音。“拍先”不懂音韵,就让他教家人唱昆曲。二姑母、大姐姐、大弟弟和阿季一大堆人一同学,大家都不识“工尺”,学的是《西楼记》。第二次“拍先”又来上课,除了阿季,谁都忘了。因此就剩了阿季一个学生了。“拍先”称阿季“二小姐”,说“二小姐只需教两遍就能上笛,是少有的”。父亲自谦“曲聋”,教他多遍,还不会唱,甚佩服阿季学得快。
吴课余有昆曲班,阿季唱小生,人家是先认工尺,后学唱;阿季是先会唱,后识工尺。周芬也会昆曲,她们用“说白”的调子说话,以为笑乐。阿季曾多次登台清唱。
曾想学医:偷看手术后2周不想吃肉 怕杀生只能作罢
在东吴,阿季还交了一个与她同岁的美国朋友陶乐珊•斯奈尔(Dorothy Snell),一个天真活泼的女孩。两人上课连座,上老校长文乃史博士的课,她俩边听课边玩。阿季双手合成船式,吹小球可绕手指转十几转,乐得笑出声来。老师发觉,叫阿季起立答问,一连问了十多道题,居然对答如流。老师无奈,让坐下来。
一次,做生物实验时,陶乐珊问阿季:“Can you swear?”(你敢咒骂吗?)阿季答:“我不能。”她得意地swear“×那娘”,阿季吓得赶快叫她低声。她惊奇说:“不能说吗?”阿季问她哪里学来的?她说是听黄包车夫说的。
一次,陶乐珊告诉阿季,她爸爸将做一台大手术,为喉部堵塞不能进食的患者插一根橡皮管子到胃里。患者已将饿死。阿季如有兴趣,她将smuggle(偷带)阿季入医院去见识。阿季洗了澡又洗了头。陶乐珊一身白衣,冒充护士,也为阿季穿上护士的白衣,戴一只圆顶白帽,混进手术室,站在不碍人的近旁。陶乐珊说:“假如你晕倒,我抱你出去。”阿季没有晕倒,她细细看了整个手术的过程。但是足足两个星期不想吃肉。
想必这次观摩给阿季留下的印象深刻,六十多年后,杨先生在北京医院陪住,偶与为钱先生手术取出一肾的邵洪勋大夫闲话,得知邵大夫解放前作为地下工作者,曾在博习医院受到保护,便讲给他听当年混入手术室事,知道如何用针缝皮肉。邵大夫说她看得很仔细。
苏州东吴大学的两个强项专业是医学预科和法学预科,前者三年毕业可直升北京协和医学院,后者可直接升入上海东吴大学法科。
阿季在振华学习时,听了南丁格尔的故事,深受感动,想学护士。爸爸说,学护士不如学医。可惜阿季虽然理科成绩门门都好,天性害怕杀生,生物实验要活剥螃蟹的壳,看那还在跳动的心。阿季替螃蟹痛得手都软了,手指都不听使唤了。全班同学都剥下了蟹壳,唯独阿季苦着脸,剥不下。这回亲眼看了一台外科手术,更使她感到自己不适合学医。
青葱岁月的初恋乌龙: 费的初恋不是我的初恋
1932年初,借读燕京手续办妥,阿季与父亲商量要北上借读。父亲不大放心,说:“你若能邀约到男女同学各三人同行,我便同意你去。”阿季果然约到周芬、张令仪两女生,孙令衔、徐献瑜、沈福彭三男生。张令仪本约定同行,但她临上火车赶到车站,变卦不走了。
1932年2月下旬,阿季与好友周芬,同班学友孙令衔、徐献瑜、沈福彭三君结伴北上。那时南北交通不便,由苏州坐火车到南京,由渡船摆渡过长江,改乘津浦路火车,路上走了三天,到北平已是2月27日晚上。他们发现火车站上有个人探头探脑,原来是费孝通,他已经第三次来接站,前两次都扑了空,没见人。
费孝通把他们一行五人带到燕京大学东门外一家饭馆吃晚饭。饭后,踏冰走过未名湖,分别住进燕大男女生宿舍。阿季和周芬住女生二院。他们五人须经考试方能注册入学。
阿季考试一完,便急要到清华去看望老友蒋恩钿,孙令衔也要去清华看望表兄,两人同到清华,先找到女生宿舍“古月堂”,孙君自去寻找表兄。蒋恩钿看见阿季,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,问阿季既来北平,何不到清华借读?阿季告诉她燕京借读手续,已由孙君接洽办妥,同意接收;蒋恩钿还是要为阿季去打听借读清华的事。
晚上,孙令衔会过表兄,来古月堂接阿季同回燕京,表兄陪送他到古月堂。这位表兄不是别人,正是钱锺书。阿季从古月堂出来,走到门口,孙令衔对表兄说“这是杨季康”。又向阿季说“这是我表兄钱锺书”。阿季打了招呼,便和孙君一同回燕京去了,钱锺书自回宿舍。
这是钱锺书和杨绛第一次见面,偶然相逢,却好像姻缘前定。两人都很珍重这第一次见面,因为阿季和钱锺书相见之前,从没有和任何人谈过恋爱。
蒋恩钿很快为阿季办好借读清华的手续。借读清华,不需考试,有住处就行。恩钿同屋的好友袁震借口自己有肺病,搬入校医院住,将床位让给了阿季。同屋的还有振华校友张镜蓉,也读外文系。
东吴结伴北上的一行五人全部通过燕大考试,四人注册入燕京就学,一人借读清华。好友周芬送阿季搬入清华。不久,周芬和蒋恩钿、袁震等也成了朋友,两校邻近,时常来往。
周芬是阿季邀约一同北上的唯一女伴,现在把她一人丢在燕京,阿季心中很过意不去。不过周芬学习认真、性情随和、善与人相处,很快就适应了燕大的学习生活、融入新的集体。她原学医预,后因家中失火,损失惨重,家境困难,学不起医,在东吴时已转入化学系。学期结束,她也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东吴。东吴大学校长杨永清一向赏识周芬,推荐她到上海中西女校教化学。当时中西的校长是杨永清的妹妹。
周芬也是阿季那种“一辈子的朋友”,一直来往,保持着友谊,周芬十分敬业,后来成为全国中等教育的四大名师之一,全国解放后被调来北京,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教材。一次,来看望阿季,说路上碰见东吴的同学,问:“见到杨季康了吗?”答:“见了。”“还那么娇滴滴吗?”“还那么娇滴滴。”钱锺书先生不服,立刻反驳:“哪里娇?一点不娇。”
杨先生说:“我的‘娇’,只是面色好而已。东吴有的同学笑我‘脸上三盏灯’(两颊和鼻子亮光光),搽点粉,好吗?我就把手绢擦擦脸,大家一笑。”
钱先生本人不也对杨先生的脸色姣好印象极深吗?他写给杨先生的七绝十章就曾这样赞道:
缬眼容光忆见初,蔷薇新瓣浸醍醐;
不知靧洗儿时面,曾取红花和雪无?
这年3月,钱锺书和阿季初次在古月堂匆匆一见,甚至没说一句话,彼此竟相互难忘。尽管孙令衔莫名其妙地告诉表兄,杨季康有男朋友,又跟阿季说,他表兄已订婚;钱锺书不问不顾定要说清楚,他存心要和阿季好。他写信给阿季,约她在工字厅客厅相会。见面后,钱锺书开口第一句话就是:“我没有订婚。”阿季说:“我也没有男朋友。”两人虽然没有互倾爱慕,但从此书信往返,以后林间漫步,荷塘小憩,开始了他们长达六十余年的爱情生活。
其实孙令衔说表兄订婚的事,也并非一点影子没有。叶恭绰夫人原为孙家小姐,是孙令衔的远房姑妈,称为叶姑太太。叶恭绰夫妇有个养女名叶崇范,洋名Julia,是叶公超的从妹。叶姑太太看中钱锺书,曾带女儿到钱家去,想招钱锺书为女婿,叶恭绰也很赞成。钱基博夫妇很乐意,但钱锺书本人不同意,及至遇上阿季,一见钟情,更坚决反对与叶家联姻。叶小姐本人也不同意,她有男朋友,一位律师的儿子。不久就和她的男友elope(私奔)了。——当时的洋学生都爱摹仿西洋小说里的浪漫式私奔。随后当然是结婚。
至于孙令衔告诉表兄说阿季有男朋友(指费孝通),恐怕是费的一厢情愿,孙令衔是费孝通的知心朋友。阿季与钱锺书交好以后,给费孝通写了一封信,告诉他:“我有男朋友了。”
一天,费孝通来清华找阿季“吵架”,就在古月堂前树丛的一片空地上,阿季和好友蒋恩钿、袁震三人一同接谈。费孝通认为他更有资格做阿季的“男朋友”,因为他们已做了多年的朋友。费在转学燕京前,曾问阿季,“我们做个朋友可以吗?”阿季说:“朋友,可以。但朋友是目的,不是过渡(as an end not as a means);换句话说,你不是我的男朋友,我不是你的女朋友。若要照你现在的说法,我们不妨绝交。费孝通很失望也很无奈,只得接受现实:仍跟阿季做普通朋友。他后来与钱锺书也成为朋友,与他们夫妇友好相处。
命运有时就那么捉弄人,1979年4月,中国社会科学家访美,钱锺书不仅和费孝通一路同行,旅馆住宿也被安排在同一套间,两人关系处得不错。钱先生出国前新买的一双皮鞋,刚下飞机就鞋跟脱落了。费老对外联系多,手头有外币,马上借钱给他修好。钱先生每天为杨先生记下详细的日记,留待面交,所以不寄家信。费老主动送他邮票,让他寄信。钱先生想想好笑,淘气地借《围城》赵辛湄和方鸿渐说的话跟杨先生开玩笑:“我们是‘同情人’。”
不知费老是怎么想的,似乎始终难忘这位意中的“女朋友”。1949年秋,钱杨夫妇应聘清华任教,与费老同事。思想改造运动中,费老自我检讨他有向上爬的思想,因为女朋友看不起他。晚年作文不顾事实,干脆说他的第一个女朋友是杨绛。本来就爱无事生非的小报就此大事炒作。一次我告诉杨先生:某小报大字标题“费孝通的初恋是杨绛”,没有什么内容,还是引的费老那句想当然的话。杨先生说:“费的初恋不是我的初恋。让他们炒去好了,别理它。”
名为杨绛的作品们:最满意《干校六记》《洗澡》
杨绛自1977年5月从西班牙原文重译的《小癞子》定稿后,开始业余创作小说,接连写了《“大笑话”》、《“玉人”》、《鬼》、《默先生》(题名后改为《事业》)等多篇小说。以致钱锺书信中跟女儿玩笑说:“得信,知又大作论文,盖与汝母之大作小说,皆肚里有货之证;若我则搜索枯肠,不成片段,德谚嘲空腹所谓‘既无臭屎,亦无孩子’。”
我请问杨先生最满意的作品有哪些?
杨先生说:“我没有满意的作品。较好的是《干校六记》和《洗澡》。好多篇中短篇小说是试图写写各种不同的人物,我都改了又改,始终没有满意。锺书认为《“大笑话”》最好。我总认为小说应写出活脱脱的人物,而故事必须自然逼真,感情动人,格调勿庸俗。”
我又请杨先生谈谈《干校六记》创作的经过。
杨先生说:“干校回来,我很感慨,想记下点干校的事。《干校六记》是从干校回来八年后才写的,是读了《浮生六记》才决心写的。我的题目和六记都照《浮生六记》的样。我是费了好大一番心思写成的,自信这部《六记》,超出我以前的作品,所以,我动笔前告诉锺书,我要写一篇《干校六记》,他泼冷水说:‘写什么《六记》!’他说没用,我还是把我想好的写了出来。我写完后给他过目,他不声不响,立即为我写了一篇‘小引’,我就知道他这回是真的觉得好,不是敷衍。平时他矢口否认敷衍,我总不大相信,因为他经常敷衍人,我对他的称赞都不相信了。他对我请看文章,总很为难。他若说我好,我不信;如果文章不好,他批评不好,又怕伤我。
“这部《六记》当时在大陆不好出,就托三联的范用帮助将稿寄香港,范用看了喜爱得不肯寄出,他自己又不敢用。后来香港《广角镜》的李国强给他来电报说,‘你再不寄,我就专程飞到北京来取稿’。范用只好寄出稿子,李国强亲自下印厂,一星期内就出版了。
“《干校六记》,若不是胡乔木同志开绿灯,不会出版的。他不知怎么看到了,就叫邓绍基传话给文学研究所许觉民,说这本书大陆上也该出。同时,在领导人宴请赵元任的会上,又对赴宴的锺书如此说,并说了十六字考语:‘怨而不怒,哀而不伤,缠绵悱恻,句句真话。 ’虽然如此,书出版后,只在柜台底下卖。丁玲说《班主任》是小学级的反共;《人到中年》是中学级;《干校六记》是大学级。”
这些事今天听来会觉得可笑,当时却确实这样,“伤痕文学”还被斥为“缺德文学”呐。然而读者毕竟有自己的鉴赏眼光,这部书在许许多多人的心里蓦然唤起对干校生活的回忆,把人们感到而不能说出的感想充分而深切地表现出来。美国首任驻华办事处主任洛德的夫人读了此书向作协提出要见杨绛,杨绛见了他们夫妇。以后美使馆请茶会、请看电影、请吃饭,不断拉拢。杨绛只去了一次茶会,末后这位夫人又请杨绛为她的作品写一篇书评,杨绛婉言拒绝了。
1983年英国《泰晤士报•文学副刊》发表W.J.F.琴纳的书评,称《干校六记》是“二十世纪英译中国文学作品中最突出的一部”。索罗金在俄文译本的《前言》中说:通过几个短篇描述的平常事件、日常的喜怒哀乐,精心刻画了中国知识分子最杰出部分的精神面貌。
社会活动的频繁,没有影响杨绛的创作和研究。她重新审校已出版三次的《堂吉诃德》,再次校阅已经出版的从原文翻译的《小癞子》,钱瑗从英国留学归来,“我们仨”重又团聚。又写了许多篇怀人忆事的散文。1986年11月三联书店出版了她的第二部文学论文集《关于小说》,收入了她在新时期的六篇论文:《事实—故事—真实》、《旧书新解——读〈萨蕾丝蒂娜〉》、《有什么好?——读奥斯丁的〈傲慢与偏见〉》、《介绍〈小癞子〉》、《补“五点文”》和《砍余的“五点”文》。其中《事实—故事—真实》作于1980年,是她这一时期的一篇重要文论,是她从多年对小说的理论研究和自己的创作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认识,她引用中外古今的典型实例说明小说是艺术创造,不是真人真事的白描写照,小说创造的规律,简括起来就是“事实—故事—真实”这样一个程式。小说即便取材于事实,哪怕是真人真事,经过小说家的艺术想像、艺术创造,性质已经改变,人物不论塑造得怎么鲜活,已不复是原来的真人,故事发展不论怎么合情合理,贴合世情常态,也只是虚构的故事。因此小说人物的经历并非作者的经历,故事如写得栩栩如真,唤起读者的兴趣和共鸣,那正是作者艺术想象、“模仿真实”创作的成功,读者完全没有必要去竭力从虚构的故事里寻求作者真身,还要掏出他们的心来看看。目前“红学”变成了“曹学”,即是这种风气的一例。
来源:搜狐读书 作者:吴学昭
 登录
登录 免费注册
免费注册 购物车
购物车 我的阅读平台
我的阅读平台